= 画家吧 =
“入”的勇气与“出”的能力——蒋开发的艺术之途
赞一下(8) 1#
flytiger2016-06-27 23:20 |
|
潘欣信 [b]一 入的勇气[/b] 在青年画家蒋开发的简历中,东瀛日本艺术名校学习、活动经历丰富,成就蜚然。如:“在日本连续举办了18次书画展,声名大振”,“1997年10月,‘蒋开发艺术促进会’在京都成立”,“1996年一1998年,全日本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现代日艺公募展’先后获‘全日本美术新闻社奖’、‘东京都足立区长赏’、‘朝日新闻社奖’”。“1998年10月一12月,‘国际艺术巡回展’先后在日本、法国、意人利分别获得‘全日本美术新闻社奖’、‘金牌’”……这些是事迹。还有在世界多个城市多次展览的成绩,如:“1983年—1992共举办9次个展,其中1990年在北京中国画研究院举办。1995年一2000年,共举办39次个展,其中在三越、崎立现代美术馆、练马美术馆、中日友好美术馆展览”,“作品还参加法国、意大利、美国、加拿大、香港、新加坡等国际性的展览。”……这样的成果,也可以说非常引人注目。加上他的身份:“世界书画家协会加拿大总会常务理事;中国文化研究中心高级画师;中国江南书画院特聘画师;浙江省青年书法家协会理事;现代日本艺术协会理事”……所有这些,足让人以为他是一个德高望重、功成名就的长者。 而实际上,与这些名声和成就相对的,却是他中国美术学院刚刚结束的“学生”身份:2008届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山水画理论与实践”博士毕业生。一方面是经历丰富、成就满身,一方面是刚刚毕业的学子,这两者身份的同时存在,足以让任何人心生好奇。但是,这正是我们可以深入认识他为人为艺的一条明径。如果你熟悉百年以来的中国绘画史,在通过一些文字和画面了解蒋开发的艺术之途后,对于他的艺术,就可以渐渐地由好奇、困惑,到理解、释然,并心生敬佩。 蒋开发的艺术经历,实际上与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在当代的发展紧密相连,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个案。几十年以来,传统与现代、笔墨与现实等等问题,始终是中国书画发展中讨论不休的问题。归纳起来,就是如何对待传统的问题。从黄宾虹、潘天寿,到傅抱石、李可染,都给出了指导性的意见。尤其是近代国画大家李可染,他在早期的一幅作品中,写了这样一段题跋:“余研习国画之初,曾作二语,自励式曰:‘用最大功力打进去’,二曰:‘用最大勇气打出来’”,在李可染众多经典的画语中,这一条是被无数后学者、理论家时时挂在嘴边,引用颇多的一句。被人传诵的原因,是因为这样的一种表述,的确是指出了中国画艺术创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当代国画创作者“如何对待传统”,指明了一条道路。 由此,我们再来看艺术家蒋开发功成名就之时又回归学院埋头深造的艺术之途,就自然可以找到先前心生疑惑的答案:蒋开发表面上看起来不为人理解的艺术历程,实际上是一个实践着画理经典,“提起最大功力打进去”的典型。 虽然这是一条真理,但说说简单,做起来却是很难的。本来,这一“进去”和“出来”的关系,在李可染先生的意思里,“打进去”,需要“最大功力”,而“打出来”,需要“最大勇气”,这是对于有胆者、有魂者,如可染先生这样的人而言(李可染另一名言即“可贵者胆、所要者魂”)。当今画坛热闹,画家芸芸,号称有百万之众,知道并理解这话的人不少,实行起来的却是凤毛麟角。究其原因,对于多数人来说,连“进去”的勇气都显得缺乏,或者说是对自己“进去”之后,能否有“功力”出来,显得不那么自信。因此,对于“进去与出来”这一艺术之险途,心生仰慕者也多,切身实践者也少。所以,对于许多画家而言,似乎这样说更为妥当:“提起最大勇气打进去,用最大功力打出来”。这绝不是要篡改李可染经典语录的意思,我只是想强调:自觉自愿的“打进去”,以求艺术更进一层的勇气,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是多么的重要!画之大者如齐白石,在1919年年届57岁的时候决心变法,曾在《白石诗草》中云:“余作画数十年,未称己意。从此决定大变,不欲人知。即饿死京华,公等勿怜”。决心变法,甚至有“饿死”的危险。可见,艺术家在艺术上改变、创新的选择绝非坦途。 而对于这一艰难的艺术抉择,蒋开发做到了。他以“犟牛”脾气,“逆流”而上(注:蒋开发笔名犟牛、逆流),为寻找、获得一种艺术上的突破、一种跳跃式的或者是根本性的发展。他在取得了诸多的成就之后,选择了一条进入学院再深造的“自缚”之途。这展示了一种艺术上的决心和为艺的态度。没有一股“牛劲”,没有对自己艺术充满自信的“牛”气,显然是难以做到的。 | |
本帖由画友自主发表,不代表本站和画家观点,据此产生的私下交易,画家及本站不承担任何责任! |
赞一下(8) 2#
flytiger2016-06-28 09:02 |
|
二 出的能力 入而能出,不仅需要勇者的胆识,还要谋略基础上的艺术实力。在当代画坛,中国美术学院的传统书画教学以注重传统,高标准、严要求而闻名。“宋进元出”四个字,以简略的话语,勾画出的却是中国画艺术研习的艰险、困难之径。因此,在钦佩他走上深造这一艰难之途的同时,我们无法不为蒋开发的“出”而担心。联想到他北京体育学院运动系毕业,先后在浙江师范大学和中国计量学院担任体育教师的人生经历,我头脑里首先想到的,竟然是少林寺十八铜人的故事。少林功夫是中国武术体系中最庞大的门派,少林一词也成为中国传统武术的象征之一。之所以少林寺因武艺高超,享誉海内外,与严进严出的“少林十八铜人”制度不无关系。“少林十八铜人”是为了防止功夫未成的少林弟子下山被人击败,辱及少林名声,因此设十八铜人于寺门,少林弟子能击退铜人即表示其功夫精湛,可出山门,闯过十八铜人阵,是成为少林寺出师弟子的证明。这虽然有武侠小说艺术化的渲染成分,但却不无道理。对于高端人才尤其“博士”的培养,“严出”是维系一个大学声誉甚至是命运的底线。当我们把蒋开发早年的艺术作品同他的博士毕业作品对比就会发现,凭借早年多方学艺、广博涉猎所打下的宽广艺术功底,中国美术学院三年时间的博士研究生的学习,他完全有能力打出这艺术的“十八铜人阵”。果然2008年中国美术学院博士生毕业展上,蒋开发凭借三张尺幅巨大的作品和博士论文《试论日本岩彩山水画的中国因素》,征服了观者和专家,顺利地“打出”了由国内顶尖的专家、学者组成的“铜人阵”。成为中国美术学院这所国内顶尖艺术高校的博士毕业生,获得了中绘画理论与实践博士学位。 通过他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蒋开发的艺术之途来说,三年的博士研究生生涯,是一个“从茧到蝶”的蜕变过程。因为他复杂的人生经历、多面的艺术取向,使得这样的蜕变内涵丰富,收获比常人更多。具体而言,有两个原因使得他完成了这样一次完美地蜕变,走上了一个崭新的艺术台阶。首先,早年多方涉猎而打下的宽广艺术基础。相对于当代众多的艺术家,蒋开发从6岁始随父亲习书画,到10岁拜西泠名家钱大礼为师学习基本功,到拜中国美术学院著名山水画教授孔仲起、花鸟画教授卢坤峰为师,还受到中国美术学院童中焘、周沧米、吴山明等教授的亲授和指点,亦曾入己故西泠印社社长郭仲选门下修书法和理论,又于有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深造水墨画和同本东京崎玉大学专研油画及西洋画理论的经历,这样的转益多师是比较少见的。因此,在这样“宽”、“博”的基础之上,对于“专”、“深”为追求特色的博士学习过程,蒋开发毫无疑问可以创造出比常人更多的成绩。 其二,蒋开发对于中国书画艺术美学的认识。在多年艺术探索中,对于艺术境界、艺术创造、艺术与时代、个性等问题,蒋开发有着深刻的认识,形成了他所简称的“随感”。但在我看来,这实际上是一位画家成熟的绘画思想。如对于“真善美”的问题,他认为:“真、善、美不但是人类精神文化追求的最高境界,更是艺术的精髓”;对于“雅与俗”的问题,他认为:“雅俗共赏的艺术品,其实难度最大。因为她的灵感最贴近人类的共同美感,这样人们对她的要求会更高因此难度更大”;对于艺术与时代的问题,他提出的观点更是别出新意:“艺术品应有时代感。但决不是盲目的追求时髦。艺术创造追求个性远远高于追求时代,因为在充分健康地发掘个性的同时,时代自然也在其中。”对于艺术个性,他给出的答案也颇具有启发性:“艺术创造在追求个性之先,首先要磨练基本功,因为没有基本功的作品其实很难说有个性。因基本功是个性外流的桥梁”……这些话语,无不闪烁着真知灼见,不经过长久的探索,难以有如此论述。 对于他的艺术风格、画面特色,美术界的一些著名人物如肖峰、孔仲起等前辈,已有许多精彩论说和高度评价,无须赘述。总起来说,他的艺术特点是先期艺术广且博,画面笔墨奔放,风格多样,处处彰显出力度和生命力;近而画面专也精,大山、阔水的画面营造之中,深得元人清、雅、逸之趣味。变热情奔放的“纵横捭阖”为含蓄内敛的“骋怀味象”。 | |
本帖由画友自主发表,不代表本站和画家观点,据此产生的私下交易,画家及本站不承担任何责任! |
【提示:注册登陆后,可以修改以上信息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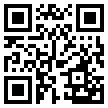
蒋开发 微官网
请保存,可以印刷到名片或画册
- 关注本站微信公众号【画家网】,拥有海量画家、美协会员、美术馆数据库。
- 了解更多资料及相关操作,请在电脑端访问本站主站(https://www.huajia.cc)
- 发现问题请联系本站管理员(微信:huajia-cc)

